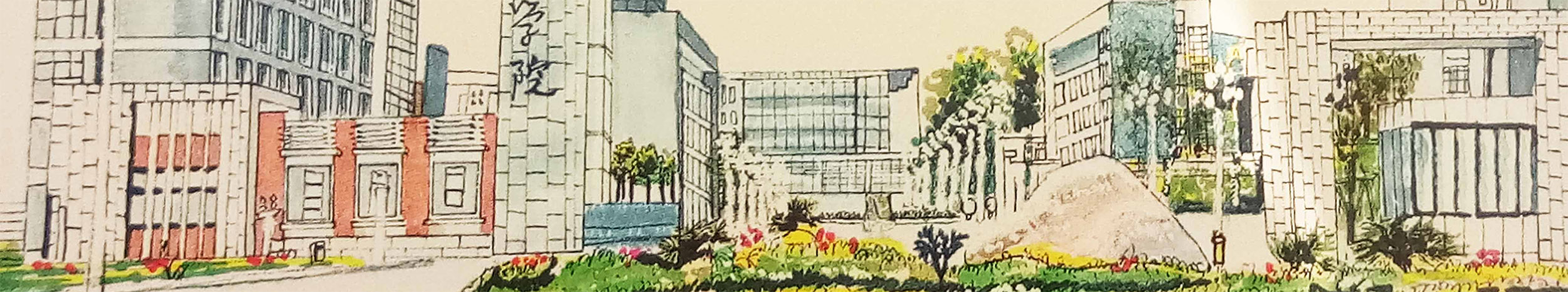《贝姨》是法国作家巴尔扎克晚年创作的一部长篇小说。故事发生在1838年的巴黎,围绕于洛·德·埃尔维男爵一家的命运展开。
旧曲又一局
——论《贝姨》中虚荣与浮华的表现与结果
181 32 王启元
指导老师:鲍俊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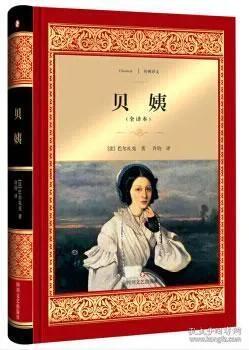
虚荣与浮华像是一张互为表里的网,网住了《贝姨》中的大多数人物,他们在这张网里自我茂盛,自我凋零,自得其乐。虚荣与浮华带给他们这样循环往复又生生不息的美梦,身为典型的他们,预示着身后还会有更多的于勒、华莱丽、贝姨......
虚荣这个在现实生活中也极其常见的词语,在书中的人物心理上得到了淋漓精致的展现。在此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是本身具有一定实力却踏进了虚荣的销金窟,由实转虚,如于勒、克勒凡;二是本身毫无实力,因扭曲的心理极力追求而导致的虚荣,如华莱丽、贝姨。这两类人在虚荣的表现上是大不相同的。
由实转虚者,为追求虚荣搭上了自己的财力、情感和性命。于勒男爵作为绝对好色者,在追求华莱丽的过程中所表现出的盲目攀比、好大喜功的性格特征,最终摧毁了他本就岌岌可危的生活。在家庭捉襟见肘的当口,阿特丽娜正发愁女儿的嫁妆婚礼开支时,于勒“被色情的利爪抓住了”,为了华莱丽四处借贷,赔上自己的工资和养老金,也要为她置办一所公寓,赢取她的芳心。而华莱丽早已看透于勒,“当他小孩子一般拿着糖高高的逗他”,也不妨碍她在克勒凡那端的无尽索取。克勒凡作为精明势力的商人,在面对华莱丽这株诱人的罂粟时,还是有着强烈的自我表现力,婚礼大操大办,邀请“顶有趣、顶上流”的人,最终人财两失,性命未保,冥顽不悟。他们虚荣的目标是情欲,是情人的芳心暗许,是竞争者中的独占鳌头。
心理扭曲者,为虚荣耗费精力、蹉跎岁月。华莱丽的目标始终是金钱和地位,她的情妇不过是她向上攀爬的垫脚石,她要摆脱和丈夫玛奈福的穷苦生活,抓住于勒这第一个机会便死死不放手,直到于勒再无任何利用价值便一脚踹开。极端自私自利的她是这场游戏中的美杜莎,绝世美颜又极端危险,可最终还是摆脱不了被圣剑斩下头颅的命运。贝姨这场闹剧的幕后操纵者,怀揣着强烈的嫉妒之心,对表姐一家由嫉妒转为仇视。阿特丽娜和奥当斯的痛苦她甘之如饴,以嫁给于勒元帅为手段完成她的复仇大业,世事难料,于勒将军的自杀直接导致了她竹篮打水一场空。伪善的面目还是埋葬在自己心里,在于勒一家病床前的照料中去了天堂。
在巴黎,利害关系迟早要分裂,生活糜烂的人永远契合无间。同样,虚荣的人们相吸相斥,在黑暗中向着更深的虚幻光芒拉扯前行;而虚荣本身和崇尚虚荣的人,在共生关系中,总有一天,人会被虚荣吞噬,成为虚荣的奴隶,不知是为虚荣而活,还是为自己而活。
浮华,多么有诱惑力又虚幻的词,末世多轻薄,骄代好浮华。浮华的表现可分为物质生活浮华和精神状态浮华,前者灯红酒绿,物欲横流,醉倒温柔富贵乡;后者自怜自恋,浮躁虚荣,不知根底。
物质上的浮华随处可见,以玉才华和华莱丽的公馆为甚者,整个巴黎难出其右。同是上流社会的女子,于勒夫人阿特丽娜在进入玉才华公馆时还是“头昏眼花,不胜惊异的把艺术品一样一样看过来”,这间公馆是巨大的熔炉,其中融化的不止是多年来的寻欢作乐,更有巨大的家业,这里所展现的是骄奢淫逸的魔力。于勒和克勒凡总纠缠在玉才华和华莱丽之间,他们为她们数不清的情妇中的二人,以家业、金钱为基底,打造出似梦似真的华丽王国。“十五年来,克勒凡之流为了糊纸的板壁,金漆的石膏,冒充雕刻等等所花的代价,可以把美化巴黎的公事全部完成”,浮华至甚,荒唐至极。
精神上的浮华以文赛斯拉为代表,他在艰苦的生活环境下、在贝姨的唠叨监督下,能雕刻出令人赞叹的艺术品,证明他是有才之人。但年少成名,风头过盛倒不是一件好事,对外拥有了名声利益,对内拥有了妻儿,人生状态达到平稳饱和时,思想中的惰性就逐渐显露。他和于勒、克勒凡一样,被华莱丽玩弄于鼓掌之间,他是华莱丽在功名利益之外寄托感情的暂时载体,他却为了这荒唐的情感抛妻弃子,同华莱丽苟且。至此,他的才华早在不知不觉间消磨在他自以为最舒适的环境下,才华散尽,不愿为江郎,却早已成了江郎。无实力依存的文赛斯拉,只能将名声寄托在虚幻的事情上,他最终成了一位空头艺术家,在交际场中十分走红,顶着艺术批评家的名号却只是一个被众人捧杀的低能儿。
无论是物质还是精神上,浮华本身就是一个虚幻的概念,它是用金钱名利堆砌起来的温柔乡,无任何实质性内核,蒙蔽了人的双眼和心智,在这场由人费劲心机构造的虚幻狂欢中,也最终由人落幕,落幕的代价也是人本身。
虚荣与浮华总是同行,为人们展现出虚荣也构造出浮华,仿佛一对孪生兄弟。因为两者互为表里,虚荣心理操控着人们不顾一切地追求浮华所在,浮华的环境又笼罩滋生出虚荣,由此往复,构成恶性循环。除非能有内部的觉醒或是外力的冲破,打破这循环,做第一个吃螃蟹和掀开铁屋子的人,或许如此,虚荣与浮华两者才会被消解沉淀,达到人性的安宁和务实,社会的和谐和稳定,国家的发展和复兴。
也许以华莱丽和于勒为中心的这一场荒唐闹剧在书中为我们描绘的年代之前就上演过很多场,我们现在所见的是巴尔扎克为我们浓缩的典型,“祖宗可以反对儿女的婚姻,儿女只能看着返老还童的祖宗荒唐”,从维多冷口中我们不仅能看见浮华虚荣的恶果,更能看见其中的祖宗本位思想,这样的社会,也该到“敢教日月换青天”的时刻了。
自我茂盛又自我凋零,自我创生又自我毁灭,虚荣与浮华带给人们的无非如此。但愿现在的我们,能从经典文学作品中,体悟落幕曲,看罢终场戏,恍然发觉原是淡抹最相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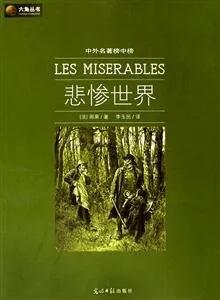
《悲惨世界》是由法国作家维克多·雨果在1862年发表的一部长篇小说,涵盖了拿破仑战争和之后的十几年的时间。
以《悲惨世界》为例析人生两难困局
181 金晶
指导老师:鲍俊晓
“无论他怎样做,他总是回到他沉思中的那句痛心的、左右为难的话上:留在天堂做魔鬼,或是回到地狱做天使。”有时命运会把人推向无法抉择的两难困局,就像冉阿让面临的一般,在天堂做魔鬼还是在地狱做天使,说是两难,难在当下无法做出抉择。说得通俗一些,但凡倾听自己的心中的声音,努力看一看内心,这个选择其实并没想象中那么难。
当一个罪犯隐姓埋名准备迎接没有敌意、仇恨的后半生时,也许会问偷一块面包就要被一辈子被定义为罪犯吗,只能说在那个社会的法制下,答案不言而喻。马德兰市长在事业稳定生活安定时,没有什么奢侈的愿望,他无时无刻不在一面追念伤怀的往事,一面庆幸难得的余生,以弥补前半生的缺憾。他生活安逸,有保障,有希望,马德兰市长也就是冉阿让只有两种心愿:埋名与立德,远避人世与皈依上帝。可是命运总不放过过得安稳的人,在商马第被误认为冉阿让即将替他在狱中服刑时,心里的两种声音正是人生现在面临的两难困局:一个阴森贪婪的声音告诉他:去烧掉烛台、忘记主教,这样就可以仍做市长先生,受到尊敬,繁荣城市,受人敬佩,继续享受欢乐和光明;一个讽刺绝望的声音告诉他:如此可以接着享受和蔼的目光、早晨的咖啡,但将有一个无辜的人穿上冉阿让的红褂子,顶着冉阿让的名字,在牢里拖着不属于自己的铁链,受尽侮辱。
人生的两难困局总会不合时宜地出现,但当心里出现第二个声音的时候,暗示冉阿让已经动摇,否则无论是万恶不赦,还是纯洁美好的人,在面临选择时心里坚定地只有一个答案时,他只会处于一个境地,又怎么会有两难困局的存在呢。蒙羞的人都渴望别人的尊重,冉阿让本不是恶魔,在他想彻底放下罪名的阴霾,生活在光明下时,出现在人生里的这一支插曲(两难选择)不打招呼地奏响了,历经脑海风暴般的心理斗争,冉阿让还是在善良的灵魂的救赎下,谱下了为善的音符。
都说冉阿让的结局是悲惨的,他做出了选择后失去了原本光明的一切,可我不认为他毫无美好的地方,他的灵魂最终没有在两难中陷入污泥,只是暂时待在了一个阴影处而已。当面临人生的两难困局时,一个选择可能会改变一生,在十字路口前害怕畏缩都不是解决办法,像冉阿让般坚定,不抱怨环境不埋怨社会,跟着自己的内心走,哪怕选择的前路是黑暗那也只是暂时,依靠自己的力量做出正确的选择,纯净美好的灵魂总会收获一片阳光。

《鼠疫》是法国存在主义作家加缪的代表作,被认为是加缪最有影响力和社会意义的作品。作品描述了在一个叫奥兰的小城发生的一场持续将近一年的鼠疫之灾。
《花冠病毒》本书是国内首部心理能量小说,是著名作家、心理学家毕淑敏沉寂五年,继《女心理师》之后第一部长篇小说,探索当代社会心灵危机的应对之策。
庚子年读《鼠疫》《花冠病毒》
1812 盛澜
指导老师:鲍俊晓
上一次,这样大规模的,举国震惊,令人谈之色变以至于封城的大规模传染病爆发,应该是2003年的非典,不过那时候我还小,对于这一切没有太多的记忆,只是听妈妈说起,那一年,从部队回家探亲的老爸,刚刚下长途汽车,还没有见到我们,就被部队紧急召回,直接被送去了军区总院隔离了半个月。甚至到去年年底之前,提起这件事,我还会没心没肺地“嘲笑”老爸一顿,但是,当这次新冠病毒真的爆发,看着住在对门的邻居家被贴上封条,而我自己也被关在家中隔离时,我第一次感受到了一种从没有过的恐惧,仿佛自己触摸到的每一个物体,吸进体内的每一口空气,都含有那可怕的病毒。正如老师在上网课时所说:“在疫情期间,看《花冠病毒》和《鼠疫》这样的灾难文学,会比平时阅读,有着更深刻的感受和思考。”
《花冠病毒》中,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袁再春主持的那些会议。在会议上,面对没有特效药可以治疗的情况,人们讨论的最多的,是如何稳定群众的情绪,毕竟,不是所有人都有着抗疫总指挥那样有着作为一位医学专家的镇定和严谨。从隐瞒真实数据到电视台循环播放抒情歌曲和自然风光,再到禁止哄抢物资。比起病患的安置再到遗体的处理,群众的情绪似乎是疫情中面对的最大的、最严峻的问题。毕淑敏女士不仅学过医,学过心理学,更是在非典时期身着防护服进入一线采访过,因此她在书中写到罗纬芝的心理状态,真的就像在此次疫情期间,我们的心理状态:在得知一天天增长的死亡数据时“觉得咽喉似被人扼住”,当看到病床不足,医护人员不足,药品不足时,即使在这样的冬天,我们也会“头上汗水涔涔”,抑郁和焦虑也在迅速的蔓延开,前段时间看新闻,看见湖北有疑似新冠病毒肺炎感染者和抑郁症患者跳楼自杀,就会觉得特别难过。我记得书中开篇写到的抗疫指挥部的会议,讨论内容是“应否对民众公布花冠病毒感染者的真实死亡人数”。经过一番争辩,决定瞒报。此后真实的死亡数字已完全与公众无关,传媒公布的,只是指挥部从心理学角度来试图稳定民众情绪而释放的的一个烟雾弹。其实从这次冠状病毒肺炎刚开始,我就对于政府公布的数字抱着怀疑态度,尤其是得知我们小区也出现了好几位患者之后。身为一个公民却没有知情权,着实让人非常气愤。但通过《花冠病毒》,我明白了这种隐瞒有时也是必要。毕竟在某些特殊时刻,民众心理恐慌造成的损失,可能比实际疫情带来的损失更甚,之前因为恐惧和抑郁而跳楼就是例子。
同样,心理的影响,在《鼠疫》中也有着鲜明的体现,尽管有人说其实这本说的“鼠疫”是暗指法西斯的势力,但是在现在新冠肺炎的背景下,我更愿意把它单纯的当做一部写传染病的灾难文学来看,况且在欧洲大地上,的的确确爆发过大面积的鼠疫——黑死病。尽管中国与欧洲的文化有着很大的差别,但是面对灾难的阴霾时,心情都是一样的。新闻记者郎贝尔因为公事被困在这个城市,他总觉得自己是外乡人,不应该困在这里。他千方百计多方奔走,用尽一切办法甚至是偷渡,只为逃出城去。“我并不相信英雄主义,我知道这并不难,而且我是懂得这是要死人的事。使我感兴趣的是为所爱之物而生,为所爱之物而死。” 主人公里厄医生对郎贝尔的举动没有表示制止,因为面对这样的状况,出现这样的行为,他也觉得没有能力去判断是对是错,是好是坏。就像这次疫情期间,有很多在武汉的外地游客,因为武汉封城而被困在了城内,他们刚开始时可能也会害怕,生气,不甘,但是,“不管我愿不愿意,我就是这城里的人了”灾难一旦降临,就不是个人的痛苦,而是集体的遭遇。朗贝尔留了下来,选择面对鼠疫,和志愿卫生防疫组织一切工作。我相信,如今,这些旅客一定会做出和朗贝尔一样的选择,留下来,为这座城市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面对疫情,人人都会恐惧,就连《花冠病毒》中的抗疫总指挥袁再春都说:“怕死,怕我死。”但是人性不仅仅有 自私的一面,也有着光辉的一面,《鼠疫》中的朗贝尔如此,现实中的我们更是如此。有一种说法,叫“文学即人学。”即文学是为了表达人的思想,人的情感,反映人的真实心理与状态。像《花冠病毒》和《鼠疫》这样的灾难文学,便是如此,他们展现了人的坚强,人的脆弱,歌颂的人的光辉,也揭露了人的自私。
当灾难来临时,人们面临的冲击极大,需要考虑的问题也就更多,从灾难的来临,到抵御灾难,再到灾难的退去,每一步,都有值得我们思考的地方。虽然毕淑敏老师在《花冠病毒》中一再强调这是虚构的故事,不要和非典联系起来,但是,有些东西却是我们不得不注意的,例如,花冠病毒的来源是冰川水,因为冰川融化,带出并唤醒了沉睡已久的病毒。冰川水的大面积融化,来源于人类对于自然的过度开发和破坏。而非典和这一次的新冠病毒,直接宿主都是蝙蝠,是由于人类过度入侵野生动物的栖息地,才使得这些原本在动物体内的病毒进入了人的身体。在灾难来临前,我们永远自诩为地球的主人,视万物为刍狗,而正是这一系列的行为,使得我们遭到了大自然的疯狂报复。从非典,到中东呼吸道综合征,到各种禽流感,再到这一次的新冠肺炎,我们永远是在疫情来临时慌乱,在疫情结束后遗忘,却从未在疫情来临前觉醒,即便这样的灾难一次又一次的席卷人类,我们却仍然不懂得尊重自然,不懂得与世间万物和谐共处。在网上有一种说法:“2003年的非典,终于教会了中国人要洗手。”虽然不知这话是真是假,但是人们似乎从不知道防患于未然,甚至在疫情已经发生的时候,仍然不知轻重,不戴口罩,外出溜达,在前几天居然还出现了扎堆喝茶的现象。
而在疫情中,药物的发现发明和审查则是一件需要考量颇多的事情,在看《花冠病毒》之前,我只知前线的医生护士辛苦,却不知,药品的研究和试验也是一件难事,《花冠病毒》中,罗纬芝大量服用了李元给的粉末2号,扛了过来,但当时医学上没有任何一种药物可以杀死病毒,这种疗法虽然相继在罗纬芝、陈天果和苏雅身上见效,想要大规模地应用于临床,却困难重重,涉及药品审批、试验数据、临床用法、医学伦理等各种阻碍。特别是医学伦理,我记得在前几天的新闻发布会上,钟南山院士也提到了医学伦理和副作用等问题,药物的研制是艰难的,在这样的情况下,更多是靠人的抵抗力和意志力来熬过病毒,我相信,在《花冠病毒》中,毕淑敏女士对罗纬芝抵抗病毒的描写,大概也是她当年在隔离区看见病人们努力活下去的真实写照吧。
疫情能够过去当然是万幸的,可是疫情过去之后呢?《鼠疫》中,随着鼠疫霍乱的消退,奥兰城再次显现出非常幸福安宁的样子,火车缓缓通过,大家齐声欢呼,可是,又有几个人能有里厄医生那样时刻保持着冷静与思考呢?对于“胜利”,里厄保持着警惕,因为他明白这并不代表着终结和安定,生活仍再继续,荒诞和苦难不会停止,他没有加入欢呼的人群,“威胁着欢乐的东西始终存在……也许有朝一日,瘟神会再度发动它的鼠群,驱使它们选中某一座幸福的城市作为他们的葬身之地。”加缪以一个旁观者的角度,借助里厄这个角色给了大家提醒,可是不知是否是像毕淑敏老师说的“人们对于痛苦的记忆总是趋向于忘记。”非典之后,吃野味的现象仍然屡见不鲜,“世上有过鼠疫的次数和发生战争的次数不相上下,而在鼠疫和战争面前,人们总是同样的不知所措”。或许,这一次新冠肺炎结束后不久,大家仍会在一片欢呼声中将它忘记,依旧会以人类自己为中心,叫嚣着征服自然,政府宇宙,可是,像毕淑敏和加缪这样的文学家们不会忘记,他们用文字记录下这一段痛苦的岁月,并用心去感受与思考。
曾听高中语文老师说过;“诗人的不幸铸就了诗文之大幸。”灾难也一样,灾难为文学提供了题材和思考的空间,但是我更希望,这样的思考空间普通人也能具有,让我们尽可能减少人为的灾难,预防可能来临的危险。
最后,我想用毕淑敏女士在纪录片《非典十年祭》中的一段话作为我这篇文章的结尾:“我觉得,病毒是一个古老的生物,我们和病毒并不是谁一定要战胜谁的关系,因为地球是一个多钟生物共存的关系。人类现在已经走到了所有物种的最顶端。我想要学会和各种生物和平共处,因为如果要说谁更早是地球的主人,病毒一定比我们更早,那么具体到一个病毒,它开始肆虐的时候,我想我们的科学家,我们要有一种更为科学的态度,来对待这个问题。这个病毒它是怎样发生了变异,这个病毒它原来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它为什么会在今天,在某个特定的时刻,这样侵袭人类,我想这些都是值得我们去考虑的。不然的话,当这个病毒发生的时候,我们不知道它从何而来,当这个病毒走了的时候,我们又不知道它从何而去。我们也不知道下一次,又会有什么病毒将来危害人类。”这里的病毒,不一定仅仅指正在的病毒,可能可以泛化到诸如战争等一切危害人类安全的事物。而这样的反思,不仅仅是属于毕淑敏和加缪的,也是属于所有灾难文学的,属于所有对于灾难有所反思的人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