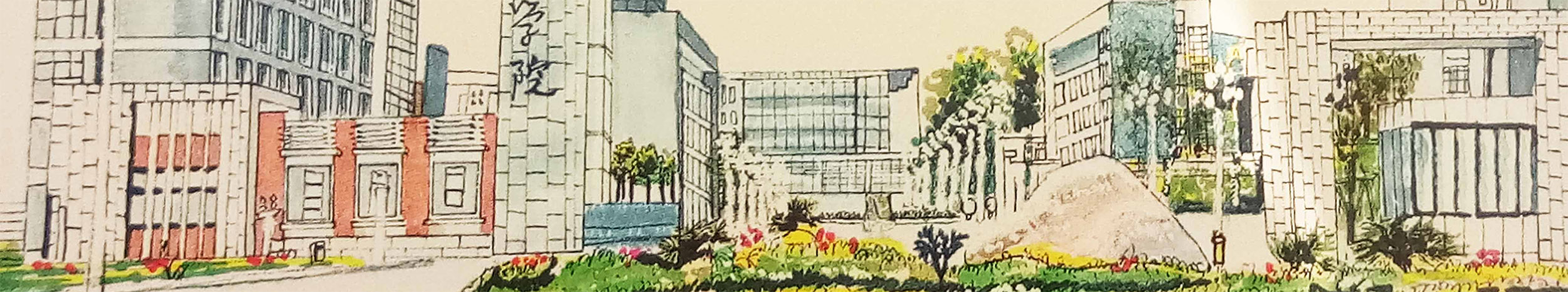“并拢手指,拱起手背,当我们用手模仿贝壳形状捂住自己的耳朵时,很快就能听到低沉而熟悉的冲刷声,那是血液流过头部微血管的声音;那是潮汐,储存在记忆里的声音。血,有海水的咸度。”我心里爱极了周晓枫的这段文字。
所有的生命都起源于海洋,我们的祖先也置身其中,说来也只有海才是我们真正的怀抱,也只有海,是唯一在重复中永不让人厌倦的事物。
有情风万里卷潮来,无情送潮归。我就站在海岸一角,看潮水消长、激荡,对这片海不离不弃,不悲不喜。潮汐,使海拥有自己的心跳,赋予海饱满的原始情欲般的生命律动。我观潮,看海巨人那喘息的胸脯,我总能从她那极端的激情感染到迷醉又紧张的战栗!
以前,我没有这种心境。
摇晃的身心就像置身大海中央的一叶扁舟,没有稳定的立足点,大海的起伏决定我的沉浮。过于置身事内,凡事总想追查原委的人,等不到来自陆地的救援,也找不到逃脱的路径。生活的不确定,让我套上了一双烙红的鞋,不停弹跳是对我无法适应的惩罚。日复一日,就像海重复这样的节奏,从雷霆万钧到精疲力尽,一次次的死去,又一次次的复活!
自从听说吴哥有最静定的佛像,慈悲的微笑可以抚平一切褶皱。知道我意识到也许我需要得到生活的宽恕。
但我跑了大半个吴哥,觉得这儿比我更陷入苦难而无法自救,我带着渴望受教的心来瞻仰佛像,却被如地狱般的惨状惊吓。这里的人甚至是孩子,都缺少完整的手脚,建筑物已倒得有些年头,遒劲的树根盘踞其上。班蒂雷斯女神像分崩离析,腰肢扭曲,五官破碎,在她身上我找不到一丝安慰。失望地在旁边的一个小书摊停下来,摊主抱着她熟睡的孩子,轻拍着的手在地上只投下三根手指头的影子,格外显眼。看见我,她咧嘴一笑,用不标准的中文轻问:“买一本吗?”我害怕对上她那一张笑容和伤口并存的脸,低头翻书。
这是一本描述吴哥历史的书。除去前几页一闪而过的风调雨顺,厚厚的一本全是苦难:在吴哥走向最繁荣时,外族入侵了。外族没有虔诚信仰,不过他们刀剑锋利。吴哥人民双手合十,却被屠杀殆尽。之后,瘟疫赶走了外族的刀剑,却让痛苦的呻吟更甚。然而苦难还是没有放过吴哥,废墟上还能上演悲剧。
十九世纪法国人“发现”了吴哥,这次“发现”如此自大,带着资本主义的优越感,妄图霸占吴哥的美。也就是在这时,寺庙被拆毁,雕像被挖走,偷盗在光天化日之下盛行。看到这里,我身上透着一层细密的汗,手抖着不敢再翻。我的苦恼在吴哥的浩劫面前,渺小得不该存在。可是还没有完,后来越南战争波及了这里,吴哥的地表上埋了无数颗炸弹,世界的野心在这里爆发了。也许一个无知的孩子在地上乱掏都会因此支付一生的健康。书的最后编者写到,所幸在所有苦难来到之前,阇耶跋摩留下了一百多个大佛头,在吴哥上空,它们一直微笑……我猛然抬起头来寻找。果然,身旁仅存的几座高塔上都有一个大佛头,在夕阳下头泛金光,面含微笑。不惊、不怖、不畏。我突然想起刚刚那位摊主的微笑,同样不惊、不怖、不畏。似乎一切都是一脉相承,但连绵不断。
微笑,是吴哥人的信仰与希望,他们将它刻下来。外族来了,它不变,它也不改。它甚至仍笑着看欧洲人来霸占自己,看美洲人来毁掉自己。几百年来,它包容爱恨,超越生死,用微笑悲悯众生。吴哥人也是如此,面对贫困、病痛报以微笑,甚至面对焦躁的游客,也用微笑去安慰。
而我,什么时候忘记了这微笑,甚至有些害怕这微笑?
我望向天空,觉得获得了拯救,因为微笑,连文明都不会消失,更何况生活中的小磨难。把信仰塑成坚固的雕像,放到高处,尽管不能飞升的肉身总要回到变化诡谲的生活中,但无奈时抬头看看,便又能获得那种静定。不惊,不怖,不畏。
临走的时候我又去看海潮,起起伏伏。当波涛如战鼓,当默默积聚的浪裹挟着百年来的气焰,大海以令人震撼的席卷之力传达着她的愤怒,她似乎渴望着某种救赎与审判。看到海鸟被忽然卷起的浪花惊起又落下,突然想起一句诗:
跳波自相溅,白鹭惊复下。
“既有云水襟怀,吐纳、承受、创造,海洋养育众生;同时也根本不屑于为残暴寻找任何借口。”大海坦然,在她的自然法则里,万物皆子。退潮了,海浪卷携着被她遗弃的孩子,涌上墓地般的沙滩。我还在眺望,极目,穷尽,水天相接之处,金光闪烁,那是佛光——普度众生,渡来、渡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