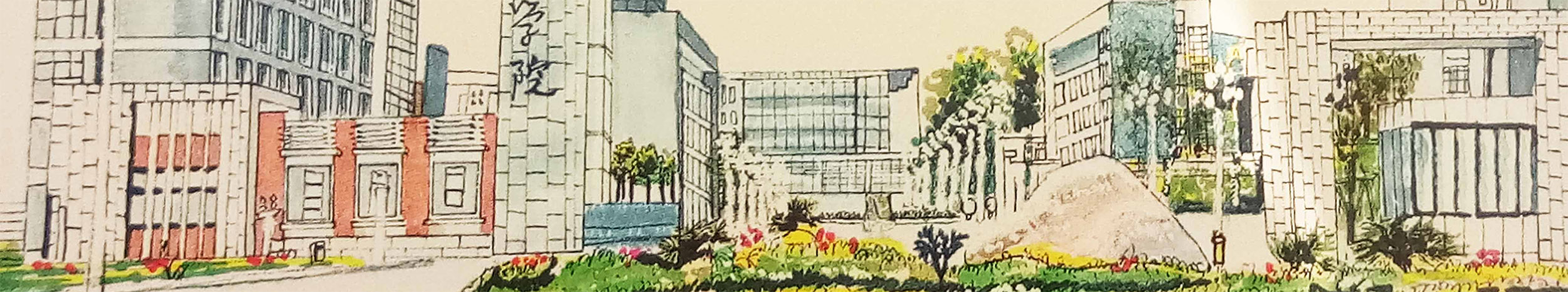每个故乡都在消逝。——王开岭
每条河流也都在流逝。
我站在碎石地上,看着栏杆外的河和栏杆里的桃柳,我想我的心是和外婆家跃起的新房一样空旷的,我知道,某样东西的离去。
想念它本来的样子。
在夏日的黄昏里,似乎大地上一切事物都醉着,只有家旁的那条河还在浪着,谁在河面上画了波浪线,谁在河面上撒了碎金?弓着背的老太照常拖了把发黄的藤椅坐在河边。有时候她会指着河岸上的那两棵依偎的桃柳,和我说,它们和你一般大。我通常会瘪瘪嘴,明明它们比我高;有时候她会盯着河里过往的啪啪抽着马达的轮船,看那些散尽天空中的烟和船尾咕嘟咕嘟的水泡,像孩子一样,我佷好奇明明开得不见的轮船老太还能看上好久,我想知道她那双被眼皮耷拉得只剩下一对小三角的眼睛能望到多远。
春天终是盼来,羞红了河岸的桃花,轻风一抚,花瓣飘进河水,让河水也遭遇了爱情。
黑皮外公会带着我和哥哥到岸边讲霍乱里依旧平静的故事,也许是一个穿红袄的姑娘,和一个穿中山装的青年。一个在岸上,一个在船上,姑娘点头微笑便许了终身,然后有了他,会讲太阳和月亮,河水与汗水的故事,大概是他挑水种田,弧着背锄地,把自己晒成了黑皮;会讲河对岸白墙黑瓦的故事,可能是对岸有个白皮外公在和自己的小外孙女讲河对岸的故事……我说:“外公,让我来和对岸的小外孙女讲我们这里的故事,我们这里有排队游水的鸭子,会讲故事的黑皮外公和一直睡觉的大黄狗…”大黄也许听到了说它的坏话,汪汪了两声,窝在草堆里的花猫一步,两步,三步地跳到了屋顶上……
夏风又吹起来了,撩动了洒着霞色的河面,柳条长得伸进了河,我猜也就只有柳窥探过河深藏的秘密。妈妈和我拎着篮子去摘桃,我望了一眼依旧坐在藤桥里的老太,她已不知岁月。妈妈说,以前这个时候,河面上都是探起的脑袋瓜,男孩子们在河中央挥动着铜色而健硕的臂膀,胆小的女孩躲在脚盘里划水,说鸭子比她们游得快,天黑的时候河面上飘着各家父母喊吃饭的声音和孩子们起水的哗哗声…
我转头看了一眼现在立在河岸的红色牌子“禁止下水,后果自负。”
妈妈还说,当年老太公乘船去工作也是这个时候。我问,然后呢?没有然后了。
也许,我知道老太的小眼能望到多远了。
一次假期,去外婆家,我发现河两岸筑起了惨白的堤坝,竖起了惨白的栏杆,白得像病床上的被单,我问外公外婆为什么,因为村委的人说河水要治理,因为掉进去的娃没有出来。我点头,对,对吧,对吗?
小姑婆家的弟弟出生了,说要看老太讲的啪啪的轮船,我说没有,想给他讲关于河的故事,看到被禁锢的河,平静地躺着,没有泪水,却不再笑了,又不知从何讲起。想起,我还没有见过对岸的女孩,还没和她讲这里的故事,鸭子,黑皮外公,还有大黄狗。。。。。。
哥哥高考结束后,舅舅说要盖新房子,把一些都推倒了,只剩下那对桃柳,地上到处都是碎石,有些掉进了河,我看到干净的河水裂了伤疤,流走的不是鲜血,是记忆和岁月。
它在流逝,带着老太的的追念,带着妈妈和外公的怀念,带着我的思念,带着所有人的纪念......
它在流逝,我知道;可是怎么办,我不知道。